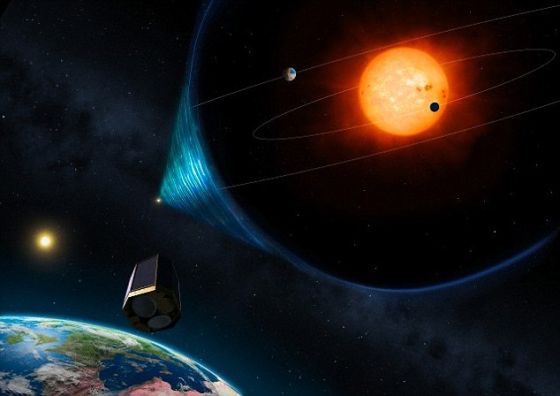这突如其来的残酷现实,使得原本平静的家庭人人身心不宁,孩子们天南地北地往家奔。忙乱中,大女婿以军人的气魄,当机立断接我和老伴来北京。无奈中,我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我们工作近40年的第二故乡。不料这一住就是8年。

8年来,我总觉得北京是属于别人的城市,我住在别人的城市里,享受着本不应该享受的幸福。亲家母来去匆匆,小住一段时间就回湖北老家忙她的农活去了。每当她来时,我心里说:“该来的总算来了,可该走的反倒不走。”当她走的时候,我又会想:“不该走的竟然走了,该走的却留下啦!”反复琢磨,我岂不是犯了“喧宾夺主”之错?
亲家母几岁时丧父,为了活命,她母亲先把她姐姐提前送给了婆家,接着就带着几岁的她投夫养女去。从此,她奔走在姐姐和继父家之间,过关居无定所、食不果腹的半流浪生活。

解放后,她嫁给村里的一个教师,生育了一儿一女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农民仍过着半温饱式的日子,但他们坚持供儿女读书。可当时农活繁重,收成不好,供两个孩子上学力不从心,不得已让女儿弃学务农,重点培养儿子。儿子酷爱学习,每周回家一罐头瓶腌菜和一些干粮,就算是一星期的伙食了。
由于刻苦用功,儿子经常参加县里、地区里的学科竞赛。回家后就对爸妈说:“还是学习好好,参赛时吃饭不要钱,还有肉吃。”高三时参加“招飞”,尽管落选了,可那次应招让他大开眼界,决定高考报军事院校。天道酬勤,1984年,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,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。
为了儿子,父亲多年忍痛不肯就医。儿子总算有出息了,自己也该去看病了。不幸的是,被确诊为胃癌晚期。这无异于晴天霹雳,让这位农家妇女哭天无泪,左右为难。万般无奈,向生产队借回了儿子上学的路费。儿子则利用课余时间打小工——扫厕所、干装卸……

第二年腊月,坚强的母亲送走了可怜的父亲,当时竟然没有通知唯一的儿子回来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。是母亲狠心,还是“钱”狠心?儿子寒假回来,还没进村就有人告诉他,他的父亲去世了。儿子连家都没回,就直奔坟地……
儿子毕业后,进入了不错的单位。亲家母苦尽甘来,成功地为祖国培养了一个合格的科技人才。谁耕种谁收获,谁栽树谁乘凉,你才是当之无愧的收获幸福的主人,住下来吧,亲家母,免得每年你们母子俩来回几趟,几千里奔波,你还晕车。每次见面,我都有许多话想对你说:“你辛苦了一辈子,却为了养了个儿子,这对你太不公平了,我于心不忍啊。”
每次我准备好了的话一出口,你马上就会说:“亲家母,你听我说,你们留得下我的人,却留不住我的心。儿子走遍天下,他的根还在我们老家;他当再大的官,他也不会忘了他老娘。他从小就孝顺,他爸身体不好,活是我一个人干,日子过得缺吃少穿。心情不好,拿儿子出气时,他抱着头说:‘妈,我不对,你打我吧,别打头,我还要用它读书。’儿了哭了,我也哭了,人也没打成。”

女婿曾经幽默地说:“那时的妈妈穷得直发毛,火气上来就打人,想打就得让她打。不顶嘴也不跑挨得轻此,跑得远撵得远就挨得狠些。”多么懂事的孩子啊!
我对亲家母说:“农闲了,像春节,你就来北京过。”她却斩钉截铁地说:“那哪能行?你不懂,过大年,家里可涌断烟火,请祖宗神位,贴年画、贴春联都要男人干。磕头烧香放鞭炮给全村人拜年,儿子必须参加。来我家拜年的人都说我家的糖果香烟比别家好。每年过年,儿子还要给村上的几家困难户送礼物。”
是的,二十多年来,女婿总是掐住时间点扛着大包小包地赶回家陪着***妈过除夕,大年初一参加村上的拜大年,这是铁的规矩。
我对亲家母说:“你也七十出头的人了,累了一辈子,地你就别种了。”

她却理直气壮地说:“不干活我浑身不得劲,你这样的日子我过不了,住在十几层高的楼上接不到雨露,晒不到太阳,人不接地气会生病的。我在家里一看电视就瞌睡,一干活吃饭也能多吃了。现在收种都有机器,有些重提到邻居帮忙干。儿女不让我去打小工。我不是为了钱,是图个热闹,到果园里,年轻人上树摘果,我坐着装箱子,不累,比坐在家里强多了。”
我情不自禁地说:“你把我说服了,说吧,我爱听。”
她一听又来兴致了,兴奋地说:“有一天,我到镇上卖菜,女儿碰上了,发火说:‘妈,你真是缺钱吗?你这些菜值多少钱?我把它全买了,你回家吧!’我指着她骂:‘你有几个钱了,就烧的说大话。老娘不偷不抢,卖自己种的菜,不丢人。’当时骂得她直哭。我不该当着那么人骂她,她也是心疼我。”
我说:“你这个妈妈当的,真有气魄。儿女都孝顺,不会缺你的钱花的。”

亲家母自信又有几分固执地说:“我不花他们钱,自己完全顾住自己了。他们给的钱我都存起来,等他们孩子大学毕业结婚时我给他们送礼。大红、二红(外孙女)上班都孝顺。孝顺就是别管我,我想干啥就干啥,想住哪就住哪。我喜欢老家,我们农村天上白云是白云,蓝天是蓝天,北京的天灰蒙蒙的,太阳不像太阳,月亮不像月亮,都一个样,一点精神都没有。树上到处是汽油味,我一闻就头晕。”
我说:“看来你是铁了心啦,不来北京长住。”
她说:“北京家里也有我一个卧室,家具、被子都是新的,我就是住不惯。儿子知道我的心,给我在老家盖了一处跟你们这一样的房子,上下两层,厕所、厨房都在屋里。我怕做饭熏黑新房子,就在后院搭了个棚子做饭。厕所的肥水都流到下水道了,我只好去好远处挑肥浇菜。儿子怕我累着了,跌倒了,又在后院盖了三间小屋,一间是厕所,一间做饭,一间放家具,我的日子不比你差。”
我说:“听你一说,我真佩服你,要不是我家老先生不能动,我就去你们那享受一下新农村生活。”

亲家母自豪地说:“我那儿比你这儿好,四季都有花看,两个月农活就干完,年轻人出去打工,老人妇女照看孩子上学,夏天哪儿凉快就去哪儿,冬天晒太阳、打麻将,晚上还有广场舞。这里的青菜不香,水也不甜,豆腐没有豆腐味。我家后院大,种有各种青菜,几种果树。青菜水果吃不完,卖钱、送人。鸡子、鸡蛋也不用买。”
我说:“我也是农村出生的,原先打算退休后找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,修个小院,在院里种花种菜、养鸡养鸭。闲时,坐在瓜棚下喝茶、看书、听音乐,树上的果子挑着吃。死了把骨灰撒在那里,山上一半,水里一半。现在想来像是在说梦话了,空的!”
听我这样一说,她又神秘地问道:“我问你,你们死了埋哪儿?”
我深思片刻,说:“我还没想好,孩子们也没问过我。好像大家谁也不想先提出这件事。”
亲家母却爽快地说:“你听我的,死了就埋我们那里,省钱还省事,孩子们上坟烧纸,一趟几个坟头都烧了。我给孩子们说,村上干部我去说,放心,问题不大。”
我想了想说:“这是我的一块心病,我家人分别在几个省工作,老伴家没有亲人。北京不是我‘安神立命’的地方。我喜欢农村,热爱大自然。”
她又问:“你喜欢什么花,喜欢什么树?”
我说:“喜欢松柏、竹子和花花。”

亲家母地说:“旱地没法种荷花,祖坟地也不兴栽竹子,栽竹子下辈人不聪明。你听我的,我爱广玉兰,咱一棵柏一棵广玉兰,隔开种,这样给坟地围一圈。”
我说:“我看行。不过,到了你那个咱不熟悉的地儿,你可要多多关照我这个远方的客人啊!”
亲家母大手一挥:“没问题。我们是今生的亲家,来世的姐妹,我们在一起,保证委曲不了你。